2018-03-14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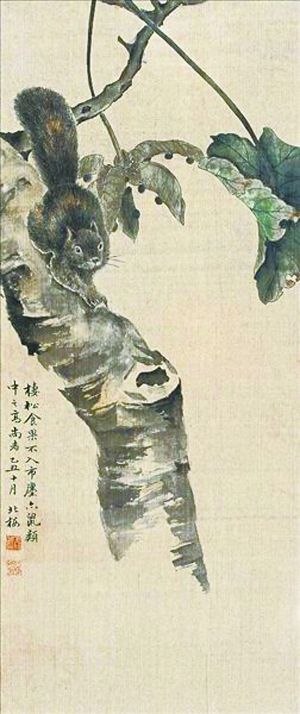
齊建秋
文人雅集是文人之間的群體性藝術活動,著名的書畫雅集活動有宋代王詵等人的“西園雅集”,明代董其昌等人的“畫中九友”,清代盧見曾等人的“虹橋修禊”。
及至晚清民國初年出現了一些有影響力的書畫會活動,如宣統年間錢慧安、倪田、王震等的“豫園書畫善會”,民國時期陳定山、孫雪泥、錢瘦鐵組織的“中國畫會”,李叔同的“文美會”,杭州吳昌碩為社長的“西泠印社”,北京金城為首的“中國畫學研究會”以及后來他兒子金開藩所創立的“湖社”等。
這些書畫家的集會,漸漸走向社會化、團體化,擁有自己的理想和社會目的,不再是文人書畫家封閉的小圈子,這些自發成立的民間書畫家社會團體,在當時都被統稱為畫會。
畫會是居于那個時代的民間藝術團體,有自己明確的宗旨和章程,有一些現代美術協會之類的雛形,但那時的畫會又不單單是個書畫家的藝術協會,它有時制定一些條例用以約束規范著書畫家道德、情操、社會和經濟活動。
畫會一般由會長、副會長、執事(相當于秘書長)組成領導層。領導層由全體畫會會員推舉產生。加入畫會需要遵守畫會章程,并由兩名畫會成員推薦,附上作品送領導層審批,并需一致議論通過才能成為畫會會員。畫會具有清高廉潔的會風,《上海通志館期刊》(香港龍門書店,1965)介紹說,其時的會風是“諸子到會,只備清茶一盞,其余未敢供應,以節浮費而重善款”。畫會強調的是切磋技藝,體現的是集體精神,重視的是慈善事業。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畫會數量最多,不光有傳統中國書畫家的團體,而且還有西畫家、漫畫家、工藝美術家的團體。沒有統一的畫會模式,藝術團體和畫會的眾多證明了當時藝術思想的活躍。
當時的上海是畫會數量最多的地方,北京的畫會活動也相當頻繁。北京是聞名中外的古都,也是政治文化中心,傳統書畫的遺存最為豐富。全國各地的許多畫家、學者、名流都匯集于此,溥儒、蕭愻、陳衡恪、金城等都是當時的代表人物。金城的“中國畫學研究會”主張的是維護傳統,保護國粹。在研究會里學術的氣氛似乎更濃一些,雖然也有為畫家賣畫提供便利的舉措,但終歸不是一種主動的意識。許多年以后“中國畫學研究會”及其后身“湖社”仍被京津一帶書畫圈內的人習慣上稱為北平畫會。
清末民初的海上畫派重要畫家楊逸在其所著的《海上墨林》(1920)一書中對上海“豫園書畫善會”的創立、活動及規矩做了一些記述,如:“書畫之余,籍可縱談今古”,參加畫會的畫家潤格要“公定潤例”,憑借畫會的名氣,畫家承攬活動所得的潤筆要“半歸會中,半歸作者”,而這半歸會中的潤例是要“存莊生息,遇有善舉,公議酌撥”。畫會對畫家的創作水平和市場知名度也給予了充分的尊重,“如遇指名專件,仍照各人自有潤例,概歸本人,與會無涉……”
從這些規矩中我們可以看出,畫會有團體概念,有文人雅興,有社會意識,有對畫家作品的市場保護。畫家在一起除了切磋畫技,還可以交流學問,每個人的潤例大家評議而定,盡可能地符合實際。依托畫會得到的收入要有一部分留儲于會中,遇到慈善事業,大家共同參議如何投入這些款項。知名畫家特別被邀請所創作的作品所得潤例盡歸本人,保護了畫家創作的積極性,也避免了平均主義,提倡了競爭意識。
畫會在書畫家群體里倡導禮義廉恥精神,要求藝術家自重,要求客戶必須尊重藝術家的人格,書畫家接受訂件按勞取酬,也要按規定行事,如“壽屏不寫”,這是因為此類活計中多有阿諛之詞,有損藝術家尊嚴。“誄文不書”,也是怕有不實之詞。“市招不應”,按現在的話講就是怕有虛假廣告讓藝術家名聲受累。
畫會是那個時期書畫家的民間藝術團體,也是帶有商會性質的經濟團體,它是自由地、自發地為書畫家組織的帶有雙重功能性質的社團,對近現代中國美術事業和書畫市場的發展有著后人不應忘記的貢獻。
民國時代社會動蕩、經濟蕭條,但中國書畫界卻出了一批名家,他們在中國美術史上書寫了不遜于古人的光輝燦爛的一頁。那個時候沒有龐大的美術家協會,更沒有書法家協會,只有清貧的、廉潔的、民主的畫會。而在這些畫會的組織者、參與者或有關聯者中卻涌現出了一批如吳昌碩、齊白石、黃賓虹、張大千、溥心畬、于非闇、吳湖帆、陳少梅等在中國美術史上永鐫史冊的名家大師。每念及此,感慨不已,唏噓不止。
(作者系著名藝術市場評論家)
注: 本站發表文章未標明來源“成功書畫家網”文章均來自于網絡,如有侵權,請聯系我們刪除,聯系郵箱:1047780947@qq.com